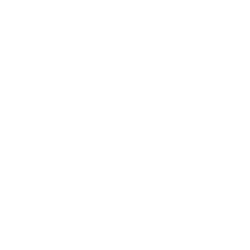笔墨——美的符号
| 2016-01-29来源:江苏省国画院 |
萧平 许多年前,我还在南京博物院工作的时候,接待过一个欧洲访问团,观赏藏画时,一位法兰西女子向我发问:“我很喜欢元代倪瓒的画,画中的境界让我向往。不知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他的画格?”我介绍了倪瓒身世,她仿佛顿然有悟:“他的画就如他的人。” 中国人说“文如其人”,画何尝不如其人呢? 作为山水画元代四大家之一的倪瓒(1301⋯1374),向以描绘简洁的太湖山水著称。就画的内容和章法而论,大约不离古木竹石和“一水两岸”、“浅水遥岑”的模式,他是极单纯而少变化的,似与所享盛名不符。然而,人们对他又极难忘怀,极为向往(甚至外国人亦如此)。 究其原因,即在“气韵”和“笔墨”。其实,气韵也由笔墨生,归根到底,笔墨二字。 倪瓒的山水画,远承董源、巨然,近师赵孟頫和黄公望,又简练变化为自我,创“折带”皴法。察其笔墨,似嫩而苍,似枯实腴,有意无意,若淡若疏,冷逸超脱,妙不可言。它既出之作者清高孤傲的襟怀,又受之山川自然的蒙养,还透着清虚无为的释道思想⋯⋯这是倪瓒笔墨给予我们的感受,是一种深层次的美的品尝和享受。 同样出自于董、巨、赵、黄的王蒙(约1310⋯1385,亦“元四家”之一)。其绘画的主体风格样式,竟与倪瓒疏简淡远形成强烈对照——它是深邃繁密的。王蒙之作,虽变化多端,然大都不离重山叠嶂,千皴万点。其笔墨,是“乱头粗服”式的,既竭尽了笔的枯、毛、松、涩、聚、散、遒、柔、灵,又竭尽了墨的干、湿、浓、淡和苍、润、清、浊,纵逸多姿,雄莽茂郁。这样的笔墨,让读者有赏之不尽之感。它是山川的至美?抑或情感的升华?它诱导人们去考察王蒙的人生,那含着隐和仕的冲突的七十多个春秋,那“虎斗龙争万事休,五湖明月一扁舟”的超逸和“不为五湖归兴急,要登嵩华看神州”的志向并存的一生。那是儒家的信守、道家的无为和佛家的空寂的融合体啊! 翻开画史,再往后看: 沈周(1427⋯1509),“吴门四家”之首。他的笔墨是朴质、沉着、浑厚的融合,又不乏苍遒有力。看着他的画,无论山水还是花鸟,就仿佛与这位画坛的忠厚长者面对了,那没有丝毫造作的和蔼真诚的面孔,便深印在心底。 “青藤白阳”,开创了大写意花鸟画的新天地。青藤即徐渭(1521⋯1593),白阳为陈淳(1483⋯1544),青藤出于白阳,白阳又得之于沈周。在这类承传有序的豪纵的笔墨中,同样存在着较大的个性差异。 如果说,沈周的天然质朴是“寄托式”的;陈淳的发展,便进入了自由奔放的“抒发式”;到了徐渭,一发而不可收,任意恣纵,就当称之为“宣泄式”了。种种样式,一一见诸笔墨,成了作者的艺术象征——浑朴的、洒脱的、狂纵的,这是美的符号。 也在这一体类中的八大山人(1626⋯1705),由皇裔到和尚,历经亡国流离的身世,形成了他孤寂癫狂的性格,也造就了他的谜一般的笔墨——淋漓而内敛,简略又奇诡。“墨点无多泪点多。”掺和着泪水的笔墨,透出的是超尘拔俗的怪味和异趣,这种美是常人难以追寻的,是不凡的。 此外,弘仁(1610⋯1663)的荒寒寂寥,龚贤(1618⋯1689)的雄浑苍郁,恽寿平(1633⋯1690)的清隽雅逸,金农(1687⋯1764)的古朴稚拙⋯⋯他们各具的笔墨样式,无一不是他们美的符号。 笔墨,是中国画,尤其是具备文人画性质的中国画的专用词。小而言之,它是中国画画法技能,即指笔法、墨法;大而言之,则反映着特定个性、学养和自然的默契,这正是中国画的核心和灵魂。笔墨,有形有状,又不确定,既无规范的程式,又无固定的相态,既造就绘画的完整境界,又具备着独立的审美情趣。处于有形、无形之间的笔墨,是一种活泼泼的生命载体,它载着自然的旋律和气韵,也载着作者的人格和精神。 对于每一位成熟的中国画家而言,笔墨就是他对美的个性追求,就是他的美的符号,古往今来,无不如此。这一符号体现着画家的发现和创造。 前贤们的种种发现和创造变成了光荣的历史遗存,这些遗存完全可以归纳为一串串美的符号,后学对于前贤的临仿,正是对特定的美的符号的借鉴和使用。借鉴、使用、发现、创造,美的符号随之越来越丰富多彩。石涛所说的“借古以开今”正合了这个规律。 笔墨进人文字,即成就了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人写字能成为艺术品,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二是中国人用的笔。”中国“书画同源”,书画也同法。后汉大书家蔡邕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这说明,书法已从字的表达概念的符号中升华为生命的单位。 赵孟頫有一首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他举例告诉人们书画的一致,最一致的便是笔墨。翁方纲题徐渭《杂花图卷》有一诗句曰:“世间无物非草书。”他把书画的一致扩大到了万物,这是发自“天人合一”观的。 徐渭笔底的花卉草木,是淋漓泼墨的极致,也是大草狂草的极致。笔者曾在天津见到吴昌硕两件晚年作品,一画葡萄,题“草书笔意”;一写风竹,题“月明满地金错刀”(“金错刀”是李煜特具的书体)。二图皆以书为画,区别仅在书体之异。笔墨之于书法,同样是美的符号。 丰子恺先生《艺术三昧》一文中说:“有一次我看到吴昌硕写的一方字,觉得单看各笔画,并不好;单看各个字,各行字,也并不好。然而看这方字的全体,就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处。单看时觉得不好的地方,全体看时都变好,非此反不美了。原来艺术品的这幅字,不是笔笔、字字、行行的集合,而是一个融合不可分解的全体。各笔各字各行,对于全体都是有机的,即为全体的一员。字的或大或小,或偏或正,或肥或瘦,或浓或淡,或刚或柔,都是全体构成上的必要,绝不是偶然的。于是我想象:假如有绝对完善的艺术品的字,必在任何一字或一笔里已经表出全体的倾向。如果把任何一字或一笔改变一个样子,全体也非统统改变不可;又如把任何一字或一笔除去,全体就不成立。换言之,在一笔中已经表出全体,在一笔中可以看出全体,而全体只是一个个体。”他认为“这是伟大的艺术的特点,在绘画也是如此。中国画论中的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这个意思。气韵生动是以笔墨生动为依托的”。 丰先生对吴昌硕书法的欣赏,又让我想起朱光潜先生说的:“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创造和欣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造出一种形象,都要根据想象与情感。”(《谈美》)所以,书画传统中载着种种不同样式的美的符号,还需要有学养、有情感、有想象力的贤者去发现,去欣赏,去研究。这是对宝贵的美的矿藏的开发! (原载于《春华秋实——江苏美学学会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责任编辑:王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