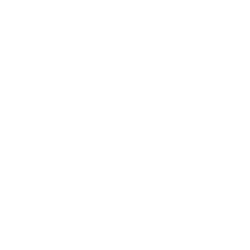游于艺——七十自述
| 2012-08-01来源:江苏省国画院 |
萧平 六十岁时,我出了一本书画集《墨缘》,同时写了一篇文字《六十自述》。我之与书画笔墨结缘,出自天性,始于童年。及长,爱好成了我的职业,持之于花甲,“不忘初心”,我似乎做到了。 光阴荏苒,不期然间,我已经七十岁了。先父母都是在这个年龄之前仙逝的,我时时念着他们。感谢他们给了我颇能持久的身躯!孔夫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杜子美诗云:“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岁,在今天已不稀奇了,但作为人生偏后的一个阶段,“从心所欲”则是理想的选择,而我心底的欲,实在离不开艺术,那是我的精神家园、快乐所在。因之,我又想到《论语·述而》篇的句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何其自由自在,得于心而应乎手,赏于心而悦乎目。“游于艺”,自然成了我七十岁书画展及珍藏集子的名称,也就是此文的题目了。 七十个春夏秋冬,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多少的人与事,多少的喜与悲⋯⋯回想起来,难免挂一漏万,“自述”亦非易事啊!我要感谢诗人吴野兄,他远在澳洲潜心写着我的传记呢! 1942年12月16日,我出生在山城重庆南岸玄坛庙仁济医院。四十九年后的1991年夏天,我曾携一双儿女重新去到那里。那是距江不远的一片高地,旧时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迁在附近,他们的摄影师,曾留下我幼年天真的容颜。其时,赵丹、白杨、魏鹤龄等影界明星,都曾与父母有往来,作家朱自清、画家司徒乔,也曾与我们毗邻而居⋯⋯小时候,我听父母讲述他们的事情,长大后,看着他们作品的时候,便自然生出一种亲切感。1977年,我在北京与赵丹、黄宗英夫妇相会,并合作了若干图画,归来告诉妈妈,我看到她脸上浮现出的欣慰之色。 我祖籍扬州,祖父子贞从事当时新兴的邮电业。据说,他是清末当地最早剪除辫子人士中的一位。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到南京家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还记得在一个天阴欲雨的日子,我陪父亲给祖父送行至雨花台附近的墓园。那是我送走的第一位亲人,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初尝了心底悲凉的滋味。 父亲鼎咸,承继着祖父的事业,而其真正的兴趣在文化和艺术,尤其于书法,有很深的功底、很高的造诣。少时我为父亲拉纸,看他作书,或行或草,或大或小,那有力的顿挫和节奏,总让我激动。母亲金一芬,安徽合肥人,来自乡村,质朴真纯,她的美而慈的面容,久存我胸,关照着我的心向着仁与爱。我是家中的长子,有两弟,和与顺;有两妹,安与迎。我的肩上负着责任,在父母先后离去的日子里,我努力维护着以往的大家庭。六年前,父亲百年、母亲九十诞辰之时,我与弟、妹们一起为父亲出版了一部精致的书法集。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先后在新加坡与家乡扬州,举办过《萧氏一门书画展》,展示父亲、我与弟、妹及孩子们三代人的作品,这些或可告慰父母于九泉的。 父亲从事的邮电工作,经常有调动,家庭便跟着搬移。记得四十年代后期在连云港有过一段不长的岁月;五十年代初又住到了宁波,为了躲避飞机的轰炸,母亲带着我与弟、妹避居于郊区卖面桥,那是我在农村度过的唯一一段时光,那艰苦却有趣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四十多年后,我还据此画了一幅《童年的回忆》。 大约自小学三年级始,直到今天,我们定居在南京,没有迁动过。为此我刻有一方印:“生于山城,长于石城。”中学的六年,在南京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度过,这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名校,曾经培养出许多名人,巴金便是其中的代表。由于这层关系,我曾有幸代表母校,去到上海巴金先生的寓所,为其画像,并在他的院子里栽下长青的树。 六十年代初,我考入了江苏省国画院专修班,受到傅抱石、钱松喦、林散之、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名师的指导。其时,画院在旧总统府内西花园的“桐音馆”中,举办过“扬州八怪”艺术研讨会,陈之佛、俞剑华、傅抱石、罗尗子等的高论,引起我对画史的兴味和对传统的思考;“新长安画派”的交流会上,又认识了石鲁和他走着的新路,那是一条开掘生活、开掘心灵的路;作为中国现代舞先驱者的吴晓邦,也曾为我们作过舞蹈语言的演示⋯⋯又让我知道,画外的天地如何宽阔。1962年夏,我有幸随江苏画家代表团(成员有钱松喦、俞剑华、亚明、张文俊、陈大羽和我)访问山东。在青岛海滨,与北京、上海、山东的一批画坛名流(吴镜汀、李苦禅、王雪涛、郭味蕖、田世光、颜地、王个簃、江寒汀、孙雪泥、朱复戡、关有声、黑伯龙、于希宁等)雅集,谈艺作画,观摩切磋。其间,我第一次登上了东岳泰山,在山巅不仅观览了日出的壮丽,还领略了佛光的神奇;又曾访曲阜,下榻幽深的孔府,仿佛穿越了千载时空,感受古代文明的丰厚。其时我年方二十,襟怀为之大开。 1963年画院毕业,进入南京博物院,在那座梁思成设计的辽式大屋顶建筑中,我埋头于数以千万计的古代书画中,从事鉴真辨伪的艰苦研究。那时,沉浸在求得新知的热情中,如饥如渴,从没有过午睡(竟延续到今天),自靠近的“金陵八家”到吴门画派、浙派、四僧、清六家与“扬州八怪”,又上溯元人和宋人⋯⋯导师是姑苏老人徐沄秋。七十年代中,又拜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并随其鉴阅了故宫及苏、浙、皖、沪数省市的馆藏书画作品。自七十年代开始,负责全省书画鉴定工作十余年,经眼书画过万。“文革”后期及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为国家抢救、保护了一批批珍贵的书画文物。 1981年,我调回江苏省国画院工作,成了职业书画家。然而,多年养成的研究习惯是不易改变的。我坚持着书法、绘画、鉴定和史论写作四项并举的方针。在绘画创作上,也兼顾着山水、花鸟和人物三个方面,不拘一格,有感而发。对于书籍和艺术真品的博览,对于大自然的体察和感悟,年复一年,从未懈怠。我相信,建筑一个广阔、深厚的基础,才有塑造成功大厦的可能。在我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将画室名“朝华馆”改为“爱莲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成了我的“偶像”。淡于名利,不倚不傍,唯真、善、美是求。 1983年,作为江苏文化艺术界第一位访问学者,我应邀去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举行演讲会和讲座,把悠久而优秀的中国艺术及我的研究心得,介绍给异国同行和爱好者。同时举办我个人的第一次画展,并考察了旧金山、洛杉矶、堪萨斯、克利弗兰、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近十家博物馆,鉴赏了几乎所有美国存藏的中国书画珍品。 1984年,我应邀访问日本,鉴阅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珍品,与日本著名南画家大山鲁牛及美术评论家远藤光一会晤交流。同年,又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艺术史系的邀请,被聘为“卢斯基金”研究员 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中国书画鉴赏”系列讲座,历时一月。 1996年春,在美国圣玛丽学院和明德大学,分别作了“中国书画艺术”的系列讲座和演示,历时两月。其间,两赴纽约在大都会博物馆观摩中华瑰宝——台北故宫所藏书画精品。 1996年秋,在新加坡艺雅鉴赏社,作“中国画的本质和中国画的鉴赏”系列讲座,历时一月余。 近三十年间,我时有应邀出席国际、国内关于书画的学术研讨会,著文并发言;也常有应约在大学、机构和团体作讲演、开讲座。所涉及的机构记得有:国家文物局培训班、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江苏省美术馆、西泠印社、澳门艺术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无锡博物馆、中欧学院、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扬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江苏中华文化学院、南京市民讲堂、杭州市民讲堂、扬州讲坛等等。我年轻时爱与老者交朋友,年华渐老时便反过来与许多晚辈交往。以往是吸纳知识,现今是感受新潮与传授经验。 我的一系列讲演,都是发自于我对中国画的基本认识。我认为,中国画的意象体系具有不息的生命力,在掌握其理法之后,便可在造物和意念之间的广阔天地里自由驰骋,薛永年教授称此为“不息论”。对立于一度发自南京的“中国画危机论”,香港《南华早报》还给过我“传统捍卫者”的称号。 关于中国书画的鉴定,是近些年随着艺术市场的发展,邀约机构经常给予我的讲题。鉴定之学是一门科学,是从许许多多实践感受与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科学。以严谨治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并举,是我对于书画鉴定所持的立场。 2008年以来。我参与了“中国画画世界”系列旅行观览与写生创作活动,连续五年,先后到过英伦三岛、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以色列、埃及、约旦、土耳其、澳大利亚、新西兰。今年又先后两度展画作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与法国巴黎,同时去了比利时、德国与意大利,游览名胜,观赏名画,体会民风,构思创作。这一活动的成果,是一年一度的写生展览并伴以写生画册。在我的认识中,中国画的传统精神,是可以置之四海而全无障碍的。因为在这一精神指导下的画法,是一种变化多端的活法。宋代词人辛弃疾说:“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功。”他说的是诗,我以为一样能够用之于画。我用中国画笔墨去描绘不同的异域风光、人物,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我画了一幅又一幅,或大或小,似皆能得心应手。实践的结果让我充满信心。 我少年时偏于内向,不喜张扬。后来慢慢开放起来。但对于明白的是非,从不苟且,用得“倔强”一词。重义轻利,不善逢迎,同情弱者,是我的性格特征。为此,我的人生路并不平坦。一些年来,世风浮躁,对于品德的漠然,对于功利的热切追逐,几遍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以风雅名的艺术圈,风雅亦所剩无几了。以“群众团体”名的相关协会,也无不忙之于竞位、谋职、争名、渔利,哪里还想得到艺术的本质与群众的需求?⋯⋯于此,我大有不适,想到苏曼殊的联语:“乾坤容我静,大地任人忙。”渐取了半隐之态,避立于边缘净地,在读书、为文、作画中获得身心的清静。 隐当有现,舍必有得。六年前,应约为扬州特殊教育学校题写校名,走近了一批聋、哑、盲童的生活。在那里,我看到了奋发于困厄中的人性之美,于是我尽力给他们以帮助,成了他们真诚的长久的朋友和师长。我因此欣慰并快乐着。 关于我的书画,风格、特征等等,似不便自说,而他论甚多,兹摘其要者如下: “萧平是一个书画兼长,山水、花卉、人物并工的多面手。他在精研鉴赏之前,由于师承傅抱石、亚明,所以作品中既洋溢着新金陵诸家的生活情味,又流露着笔端聪明,在运用中国画范式而渗入写实主义造型能力上也已远胜古人。在精意鉴赏之后,萧平由于对传统的深入研讨,开始由本师而上溯宋元明清诸家,还因为他雅善书法,善于在书画的联系中相参妙悟,因而别有所见。他的书法幼承家学,以汉隶及孙氏书谱筑基,尤爱行草,取法黄山谷及明末诸家,追求自然放逸,尤喜在用笔迅疾中出之以清劲跌宕,自成一体。这种书法造诣,使他在许多画家还不能越出写实主义雷池或只追求一笔一画的形式美之际,已对笔墨运动中的抽象表现力有了较多的了悟,认识到中国画的意象美,妙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在画内与画外之间。”(中央美院教授薛永年:《精鉴赏而善书画——跋萧平书画集》) “他在艺术鉴定和研究上所花费的精力,他不懈地体察和感悟人生与自然,正是为构建他个性风格打下坚实的基础。萧平的绘画创作不定格于一个品种,他兼顾山水、花鸟和人物三个方面,坚持从生活出发和有感而发的原则。早期作品重师承,广泛吸收前人经验,可谓‘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为我所用,在尝试各种技法中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寻找个性的表达方式,逐渐形成他自成一体的儒雅、平实、柔和的绘画作风。唯其不露锋芒,乍一眼看似平常,但只要稍细心阅读,便会发现他不凡的艺术功力和独特的艺术匠心,其中包括以书法为功底的笔墨修养,以及浓厚的文化底蕴,作品经得起品评、琢磨和推敲。显然,这既是他学养的自然流露,又是他个人性格的真实反映。”(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萧平的绘画样式》) “他的艺术魔盒里似乎储藏着取之不尽的手段:时而思接千载,时而瞬间感发;时而传统法度,时而造型意识;时而以意造境,时而对景写真;时而‘山水’,时而‘风景’;时而古人绣像,时而亲近掠影;时而氤氲水墨,时而绚烂色彩;时而挥毫,时而双勾;时而意象,时而具象⋯⋯他破了派系藩篱,超越观念禁忌,古今共存,中西并收,信手拈来,抒写感动。然而,尚古情怀永远是萧氏审美情致的主调,画面里的淡远诗意,闪烁的是一位中国现代文人幽古的心灵之光。” “萧平巨榕似的立体根系已清晰地呈现出三个层次:集书法家、画家、鉴定家、史论家、收藏家于一身,是第一层次;书法之诸体并举,绘画之山水、花鸟、人物皆擅,是第二层次;画无古今,法无定法,一画一法,是第三层次。”“他的书、画、鉴、藏、论为主根的三个层次并不各自孤立,而是交融互济,相得益彰,从而亦构成萧平‘势欲荫覆天下’的整体修养。其书法之萧飒,飘入花卉;鉴赏之所得,砌入山水;作书作画与鉴书识画两相共赢;作书作画、鉴书鉴画、评书评画比肩齐进。”“他的研究特色,与重史实考据的史家和善于逻辑思辨的论者不同,他的文史之思紧紧结合着他的书画创作与鉴赏的实践体验,图像与概念、表象与玄机、情感与哲理互为表里;重画脉、作风、品格,叙史兼及评画。文辞清朗,有古风,每有识见,娓娓而谈,导人作美的巡游。他的理论表述尤显真切,往往予人运于手、美于目、了于心的艺术触摸感。”(西安美院教授程征:《古榕·萧平》) 论者中有老友,亦有仅晤数次的长者,还有从未谋面的同道,他们都是专门的书画史论家。谢谢他们!然而,面对褒奖,我不禁脸红,生出了些许愧色。
自1988年以来,我在国内外举办过十八次个人书画展,美国两次,新加坡一次,香港两次,澳门一次,南京五次,扬州三次,无锡、常州、徐州、金湖各一次。参加的各种联展,约超过七十次,遍及亚洲、美洲、欧洲和澳洲。作品被国内外十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出版书画集六种。专著有《山水画传统技法解析》 我有收藏的癖好,主要是书与画,不论古今也不分冷与热,更不以官阶、时名论高低。我所看重的是作品载着的艺术成分与研究价值。我的这一爱好,大约源自先父,虽然他的收藏大都在战乱与变迁中流失,但他的兴趣最早感染了我。近二十年中,大批艺术品涌向市场,我有了鉴别选择的机缘,藏品也与日俱增。我的选择重点在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文徵明、陈道复、董其昌、萧云从、八大山人、石涛、龚贤、胡玉昆和金陵诸家、扬州八怪及相关流派、海上画派、新金陵画派、女性书画家、僧人书画家、名人信札等。我特别重视那些可以给画史补白或被画坛冷落、遗忘的有价值的人物及作品。有了藏品,观赏、借鉴是必然的,还有翻阅书籍资料与研究作文作论。因之,我了解了许多、发现了许多。这里真有无尽的快乐。 青花瓷也是我喜欢的,也略有涉,因为是贤妻邹正玉研究的项目,水墨与青花的相互映照,构成了我们家庭的一道风景。她是黄公望的同乡,常熟人,初学苏州评弹,后专事古代瓷器的研究与鉴定,是古瓷专家王志敏的高足。曾先后供职于南京博物院和江苏省文化厅。1968年我与正玉携手人生组成家庭,已经走过了四十四个春秋。1993年我们银婚之际,邦达老师曾作《忆江南》相贺,词曰:“江南好,鹣鲽此绸缪。论艺偏擅辨古器,挥毫从见出新猷,二十五春秋。” 我们有一儿一女。子戈、女玉,皆毕业于美术学院,能书画、通鉴赏,也从事相关行业。现在他们又有了一儿、一女,岑岑与暄暄,同龄五岁的小姐弟,常常是我们的开心果,也是我为画的对象。 毕竟年届七十了,我时会想起老杜的名句:“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然而,七十岁,对艺术的跋涉者而言,还有漫长的路程在前。某些方面,甚至刚刚了然有悟,方才初尝甘苦的滋味⋯⋯人生和事业,是在矛盾中和谐统一的。七十岁对于我,或许是一个新的起点。更合理地安排时光,更从容、自由地在生活与艺术的天地中漫游,是我的愿望。 2012年初秋于石城爱莲居 责任编辑:王洁 |